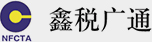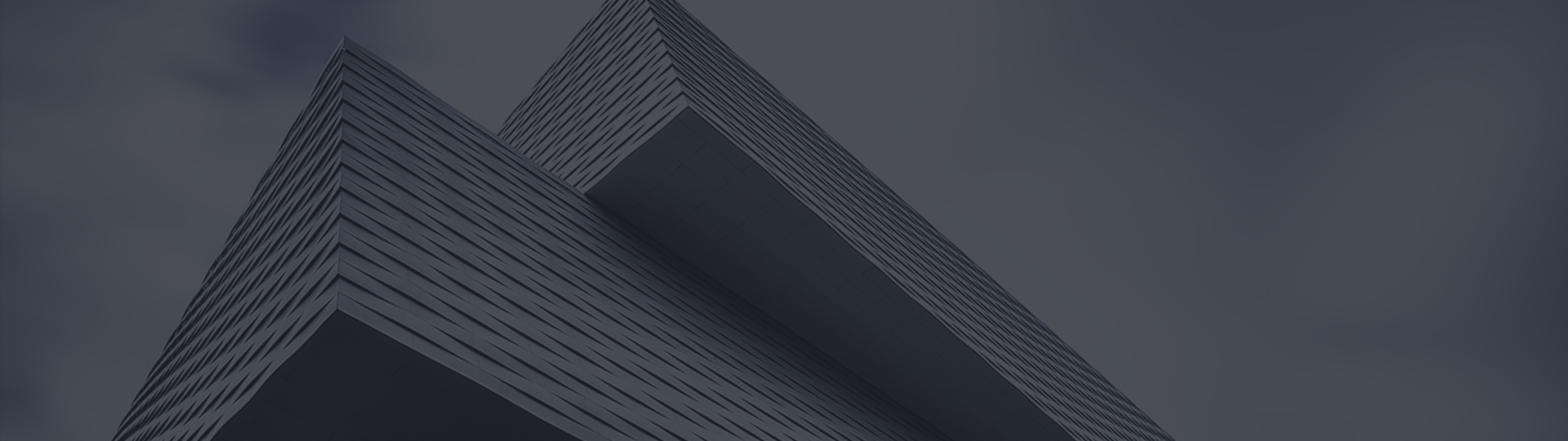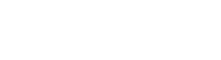最高法執行環節稅收優先權裁定的法理與影響分析
筆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對潘某股權轉讓案的裁定,以司法釋法方式明確了執行環節產生稅款的優先屬性,填補了動產執行中有關規定的空白。
“先稅后證”是我國一項重要的稅收征管制度,旨在確保國家稅款及時入庫,防止稅款流失,但在司法實踐中常與民事擔保物權產生權利順位沖突,往往會產生爭議。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最高法)對潘某股權轉讓案作出執行裁定,以司法釋法方式明確了執行環節產生稅款先行入庫的優先屬性。筆者認為,該裁定填補了動產執行中有關規定的空白,通過利益平衡重構了動產司法拍賣執行分配規則,具有重要意義。
裁定的要旨及法理邏輯
案件基本情況
2020年3月,A公司與潘某簽訂合同,約定A公司借給潘某5000萬元,借款期限1年,潘某將其所持某上市公司的1640萬股股票作質押擔保。債務履行期屆滿,潘某僅償還了利息未償還本金,A公司將其起訴至法院。Y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Y市中院)二審判決認定潘某違約,應當向A公司償還借款本金并支付違約金。2022年11月,因潘某未履行還款義務,Y市中院拍賣了潘某質押的股票,取得7409.8萬元。
次年12月,Y市中院函請Y市Z區稅務局確定因本次拍賣交易應繳納的稅費。Z區稅務局答復,按規定潘某取得的司法拍賣收入應繳納個人所得稅1259.7萬元。2024年6月,Y市中院作出《通知書》,告知Z區稅務局,根據稅收征管法第45條規定,稅務機關征收稅款,稅收優先于無擔保債權,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由于A公司享有的債權屬于有擔保債權,應當優先于稅收受償。
Z區稅務局提交《執行異議書》,請求停止執行《通知書》,優先扣繳司法拍賣中產生的個人所得稅1259.7萬元,未得到支持。Z區稅務局向S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S省高院)提出執行異議復議,S省高院裁定撤銷Y市中院作出的執行裁定和《通知書》。A公司不服,以擔保債權應優先于稅收受償等為由,向最高法申請執行監督。2025年4月,最高法作出執行裁定,駁回A公司的請求,明確司法拍賣產生的稅費應優先于擔保債權受償。
裁定的法理邏輯
一是突破有關法律關系的定性。司法拍賣屬于強制執行措施,具有公法性質。本案中,最高法突破司法拍賣的公法行為定性,將其界定為“特殊形式的交易行為”,認為其與商業拍賣在民商事法律關系本質上具有同質性,對買賣過程中產生的交易金額需依照稅收法律法規的規定征收稅款。在司法拍賣中基于本次交易形成的稅費類似于拍賣費用,在性質上屬于處置財產的實際費用,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34條“委托拍賣、組織變賣被執行人財產所發生的實際費用,從所得價款中優先扣除”的規定,予以優先扣除。最高法對該案作出的裁定文書特別指出,該稅費性質不同于一般稅收債權,而是屬于“處置財產的必要成本”,在執行分配中具有費用優先的屬性。
二是秉持利益平衡原則。最高法對本案的裁定通過“債權人合理預期限制”理論構建了利益平衡機制:無論申請執行人是否對被執行財產享有擔保權利,其可受清償的合理預期都應當是被執行財產處置后的價值,而司法拍賣過程中產生的稅款是處置拍賣財產產生的,屬于為了實現所有債權人共同利益而產生的必要費用,這些必要費用應當優先支付。故A公司基于質押權可主張的優先受償范圍,不包括因本次拍賣產生的稅款。筆者認為,該論證邏輯既保障了國家稅收債權,又避免了對擔保物權制度的過度沖擊。
法律適用的排除性說明
最高法對本案的裁定明確排除適用企業破產法第113條關于稅收債權順位的規定,指出破產程序與強制執行程序在債權清償邏輯上存在根本差異。同時,否定本案適用民法典第187條關于“民事主體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規則,強調本案稅費產生于財產處置環節,而非同一法律行為的多重責任競合,通過有關法律適用的限縮解釋,進一步明確了執行環節稅收優先權的特殊規則。
裁定可能產生的影響
筆者認為,最高法對本案的裁定可能會在多方面產生積極影響。
其一,消除清償環節涉稅爭議。該裁定確立了“交易稅費→擔保債權→普通債權”的執行分配序列,將稅收優先權的適用場景從常態交易擴展至強制執行領域。在動產執行場景中,明確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等流轉稅及個人所得稅屬于“處置必要費用”,填補了民事訴訟法執行程序中稅費清償的規范空白,形成與不動產“先稅后證”制度相銜接的全財產類型稅收保障體系。
其二,推進稅收共治。在該案裁定中,最高法依據稅收征管法第5條關于“各有關部門和單位應當支持、協助稅務機關依法執行職務”的規定,推動建立與稅務機關協同的工作機制。具體表現為:法院在拍賣詢價階段向稅務機關發出《稅費核定協助函》,稅務機關在法定期限內出具《稅收優先權認定書》,雙方通過建立拍賣信息共享平臺實現數據互通,形成“稅費預核定—拍賣款提存—優先劃繳”的管理模式,在提升執行效率的同時降低爭議發生率。
其三,拓展稅務執法依據。該裁定將“先稅后證”規則從不動產權屬變更的“證前控制”環節,延伸至動產司法拍賣的“執行分配”環節,客觀上拓展了稅收征管法第45條的適用領域。筆者認為,實務中,稅務機關可依據該裁定的精神,對資產抵債等特殊交易中產生的稅費主張優先扣除,形成“交易發生—稅費產生—執行優先”的征管邏輯,使稅收優先權制度從“事后追繳”向“事前控制”轉變。
其四,促進地方稅收保障立法。最高法對該案作出的裁定文書援引某省稅收保障條例中“司法拍賣涉稅事項協同管理”的規定,為省級層面稅收保障立法提供了司法實踐支撐。筆者認為,各地可參照該裁定明確的規則,在地方立法中增設“法院協助稅務機關核定拍賣稅費”的條款,明確稅務機關在執行程序中的權利主張路徑,推動形成“國家法律—司法解釋—地方規章”三位一體的稅收保障規范體系。
其五,推動有關經營主體考慮稅收因素。該裁定表明,債權人在評估擔保財產價值時需考慮稅收扣除因素。專業評估機構已開始根據《資產評估執業準則——不動產》《資產評估執業準則——金融不良資產評估》,采用“可變現價值=拍賣價款×(1-綜合稅費率)”的公式對擔保資產進行測算。以本案為例,A公司在設定質押時若考慮20%左右的綜合稅費率,其實際可獲擔保債權額度應調整為5927.84萬元(7409.8×80%),與借款本金基本匹配,可避免因稅費扣除導致的債權實現不足風險。該裁定也會推動參與司法拍賣的投資者考慮稅費因素,如在投資收益測算中區分交易環節稅費及持有環節稅負,前者包括增值稅及附加、印花稅、個人所得稅等,要在拍賣款中優先扣除;后者如企業所得稅,可納入年度匯算清繳。通過建立考慮稅費因素的決策模型,投資者可降低因稅費支出導致的回報縮水風險。
對主要參與主體的建議
基于該裁定確立的執行環節產生稅款優先規則,筆者建議債權人、稅務機關、司法機關三個主要參與主體通過建立稅費風險防控模型、調整制度流程、完善裁判規則等措施與之相適應。
于債權人而言,在設定擔保債權時要充分考慮司法拍賣中的稅費優先扣除因素,委托專業機構評估擔保財產在扣除稅費后的實際可受償價值,合理確定債權金額。另外,可考慮在擔保合同中約定司法拍賣中的稅費承擔條款,降低自身風險。
稅務機關可主動與法院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及時向法院提供稅收政策解讀和稅費計算依據,協助法院在拍賣程序中準確扣除應繳稅費;制定針對司法拍賣的稅費征繳操作規范,明確從法院發函到稅款入庫的全流程工作標準,提高征繳效率和準確性,并加強對司法拍賣市場的稅收監控,確保有關稅款應收盡收。
地方各級法院應按照最高法確立的司法拍賣產生稅款優先受償規則,優化司法拍賣款分配流程,確保優先扣除拍賣環節產生的稅費。同時,加強與稅務機關溝通協作,及時向稅務機關通報司法拍賣進展和涉及稅費的征繳情況,與稅務機關共同解決司法拍賣涉稅費問題。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最高法在本案裁定中通過發揮司法能動性填補了執行環節稅收優先權的空白,以案例形式確立了類案處理標準。實踐中,對于不動產的處置,因按規定繳納相關稅費后才能辦理不動產過戶手續,一般由法院從拍賣款中扣繳處置費用。對于動產等其他財產而言,尚無明確規定。本案中,最高法將司法拍賣股票產生的稅費定性為財產處置必要費用,優先于擔保債權,明確了該類交易產生稅費的性質和清償順序。建議在稅收征管法修訂中吸收有關稅收優先權規則。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青島市稅務局)